冶詩人與哲學家於一爐的世紀先驅:電影大師楊德昌(上)

文/李幼鸚鵡鵪鶉
 《光陰的故事》他導演其中一個短篇〈指望〉。有限篇幅、小品格局,竟能常常常無聲勝有聲,結合音樂與影像,散發出台灣電影中少有的詩意。藉著少女(石安妮飾演)成長的身體生理(譬如月經初臨)經驗,對容貌俊美、裸著上身的大學男孩(孫亞東飾演)的看與想,簡直是台灣電影中的女性觀點的先驅,讓男「看」、女「被看」的關係對調、意義非凡。
《光陰的故事》他導演其中一個短篇〈指望〉。有限篇幅、小品格局,竟能常常常無聲勝有聲,結合音樂與影像,散發出台灣電影中少有的詩意。藉著少女(石安妮飾演)成長的身體生理(譬如月經初臨)經驗,對容貌俊美、裸著上身的大學男孩(孫亞東飾演)的看與想,簡直是台灣電影中的女性觀點的先驅,讓男「看」、女「被看」的關係對調、意義非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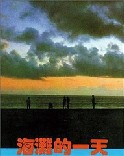 眾習慣的篇幅,更要千辛萬苦突破台灣電影院所能接受的放映時間與場次安排。在電影檢查打壓方言、禁止本土母語的年代,於片中大量使用台語(河洛話);在外語被簡化等同英語的當時台灣電影生態,首開風氣讓片中德國女孩講德語、讓女鋼琴家(胡因夢飾演)跟她用德語交談(就像13年後讓法國女孩在《麻將》裡講法語),讓台灣與非英語國度跳脫淪為美國語言、美國文化殖民地的困窘。
眾習慣的篇幅,更要千辛萬苦突破台灣電影院所能接受的放映時間與場次安排。在電影檢查打壓方言、禁止本土母語的年代,於片中大量使用台語(河洛話);在外語被簡化等同英語的當時台灣電影生態,首開風氣讓片中德國女孩講德語、讓女鋼琴家(胡因夢飾演)跟她用德語交談(就像13年後讓法國女孩在《麻將》裡講法語),讓台灣與非英語國度跳脫淪為美國語言、美國文化殖民地的困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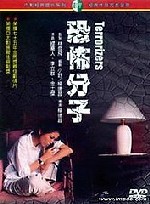 《恐怖份子》(小野編劇)形式奇詭,複雜辯證,多面向省思深刻睿智而又引人入勝,讓台灣觀眾也讓國際影壇驚艷,開展全世界對台灣電影刮目相看的先河。香港評論家金炳興、羅卡(劉耀權)、李焯桃爭相向國際影人大力推薦。詹明信還有專文分析、讚賞。片名簡單卻自有深意(香港影評人羅維明解讀「人人都是恐怖份子」而非片中某個人而已)。片尾兩個結局令人大開眼界、耳目一新,一是潛意識、夢一般的主觀心理寫實,丈夫(李立群飾演)殺死妻子(繆騫人飾演)的情郎(金士傑飾演);一是客觀寫實,丈夫舉槍自殺。《恐怖份子》人物繁多,楊德昌雙管齊下,經由女作家(繆騫人飾演)的文學創作以及少男(馬邵君飾演)的頻頻拍照,後設電影般省思藝術工作者的洞見與不見、刻意努力與偶然天成。大張巨型照片由多張小照片組成的「分」分「合」合,或是女作家在象牙塔內寫小說而窗外竟是工人在高空吊架上清洗大廈玻璃窗,楊德昌的中產階段高品味可貴在於深知中產階段的侷限與不足,不流於自得其樂,反倒有所質疑、有所批判。文藝少女自殺未遂,躺在救護車上的心聲獨白「我不要活了…」那場戲,「聲音」持續,「畫面」剪輯轉為阿飛少女在家裡講電話,鏡頭巧妙避開阿飛少女「正在講」,但見她掛上電話另外撥號,鏡頭移向她身旁窗戶,卻是粗暴腔調用髒話恐嚇對方。觀眾你我起先以為柔聲是少女自殘心語,兇悍聲調是阿飛少女在放話。隨後發現未必,倒像是:自殺告白是兩位少女「共用」的台詞,文藝少女是真心,阿飛少女是在電話中唬人;阿飛少女卻一人可以「通吃」兩種聲調、兩類對白(能文能武?!)。楊德昌不必仿效雷奈、不必抄襲高達,功力與境界三人已經並駕齊驅,辯證了「聲音」與「畫面」!何況還有些人盛讚他與安東尼奧尼遙相輝映。
《恐怖份子》(小野編劇)形式奇詭,複雜辯證,多面向省思深刻睿智而又引人入勝,讓台灣觀眾也讓國際影壇驚艷,開展全世界對台灣電影刮目相看的先河。香港評論家金炳興、羅卡(劉耀權)、李焯桃爭相向國際影人大力推薦。詹明信還有專文分析、讚賞。片名簡單卻自有深意(香港影評人羅維明解讀「人人都是恐怖份子」而非片中某個人而已)。片尾兩個結局令人大開眼界、耳目一新,一是潛意識、夢一般的主觀心理寫實,丈夫(李立群飾演)殺死妻子(繆騫人飾演)的情郎(金士傑飾演);一是客觀寫實,丈夫舉槍自殺。《恐怖份子》人物繁多,楊德昌雙管齊下,經由女作家(繆騫人飾演)的文學創作以及少男(馬邵君飾演)的頻頻拍照,後設電影般省思藝術工作者的洞見與不見、刻意努力與偶然天成。大張巨型照片由多張小照片組成的「分」分「合」合,或是女作家在象牙塔內寫小說而窗外竟是工人在高空吊架上清洗大廈玻璃窗,楊德昌的中產階段高品味可貴在於深知中產階段的侷限與不足,不流於自得其樂,反倒有所質疑、有所批判。文藝少女自殺未遂,躺在救護車上的心聲獨白「我不要活了…」那場戲,「聲音」持續,「畫面」剪輯轉為阿飛少女在家裡講電話,鏡頭巧妙避開阿飛少女「正在講」,但見她掛上電話另外撥號,鏡頭移向她身旁窗戶,卻是粗暴腔調用髒話恐嚇對方。觀眾你我起先以為柔聲是少女自殘心語,兇悍聲調是阿飛少女在放話。隨後發現未必,倒像是:自殺告白是兩位少女「共用」的台詞,文藝少女是真心,阿飛少女是在電話中唬人;阿飛少女卻一人可以「通吃」兩種聲調、兩類對白(能文能武?!)。楊德昌不必仿效雷奈、不必抄襲高達,功力與境界三人已經並駕齊驅,辯證了「聲音」與「畫面」!何況還有些人盛讚他與安東尼奧尼遙相輝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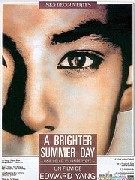 春群像,冶懷舊、成長、記憶、電影夢、流行音樂鄉愁、史詩手筆於一爐,「聲音」與「畫面」又更進一層地辯證。本片非但指控「國家迫害個人」,更能省思、類比「男性沙文打壓女性」如出一轍。台灣社會常有錯覺,以為本省與外省對立,本片卻高瞻遠矚,外省族群既多元又彼此各有衝突矛盾(公務員人家的子弟與軍方眷村兒郎有時水火不合),有時卻跟本省人(或幫派)合縱連橫。有些人以為片中「小四」(張震飾演)是楊德昌的化身,畢竟電影?進了導演自身少年時的許多經驗。楊德昌委婉否認,讓喜歡對號入座的人深受起發、自慚形穢:他表示導演必須關愛、了解自己片中的每一個角色,多為他們設想,塑造出來的人物方才真實、生動、感人。所以,片中男女老幼,尤其那些少男少女,無論怎樣恩怨情仇,他都愛啊!每一個都可以是楊德昌的化身啊!無數個楊德昌的自我辯證啊!
春群像,冶懷舊、成長、記憶、電影夢、流行音樂鄉愁、史詩手筆於一爐,「聲音」與「畫面」又更進一層地辯證。本片非但指控「國家迫害個人」,更能省思、類比「男性沙文打壓女性」如出一轍。台灣社會常有錯覺,以為本省與外省對立,本片卻高瞻遠矚,外省族群既多元又彼此各有衝突矛盾(公務員人家的子弟與軍方眷村兒郎有時水火不合),有時卻跟本省人(或幫派)合縱連橫。有些人以為片中「小四」(張震飾演)是楊德昌的化身,畢竟電影?進了導演自身少年時的許多經驗。楊德昌委婉否認,讓喜歡對號入座的人深受起發、自慚形穢:他表示導演必須關愛、了解自己片中的每一個角色,多為他們設想,塑造出來的人物方才真實、生動、感人。所以,片中男女老幼,尤其那些少男少女,無論怎樣恩怨情仇,他都愛啊!每一個都可以是楊德昌的化身啊!無數個楊德昌的自我辯證啊!本文轉載自破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