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幼鸚鵡鵪鶉
乍看起來,《
恐怖份子》頂尖的形式實驗與知性洞見,跟《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溢滿懷舊鄉愁的史詩巨構與個人記憶、時代歷史的可能傾向感性、抒情,彷彿互為鮮明的對照。其實這種兩極化的區別與分割,既粗糙又粗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依然不乏走在所有台灣(甚至世界)電影尖端的鋪陳方式(譬如小四與Honey初見的那場戲,長時間鏡頭無論場面調度或是攝影機運動都出神入化令人驚歎),以及不同凡響的形式風格(譬如建中教室有個場景是樓梯、走廊的那面反光的綠牆小四與小明的身影映照在牆上模糊得好似印象派的油畫但更幾近全然無法分辨是誰的抽象畫,你我聆聽他倆對話而不見清晰版的本尊,既是畫面中的人物發聲卻又根本就是畫外音,明明白天你我看不清楚是誰卻能從聲音、從談話內容知道是誰跟誰,隨後鏡頭方才緩緩移向這兩人,相當奇特的「聲音」與「畫面」的分析辯證省思!)。有趣的是,王柏森(原名王宗正)在片中扮演Honey的弟弟條子,要為自己發聲,而且為片中的男童小貓王(王啟讚飾演)幕後代唱,一位演員用了兩種或者更多(因為條子也會唱)種聲音來表演。
台灣電影開拍,一般會有開鏡儀式,通常上香拜神、導演與主要演員到齊讓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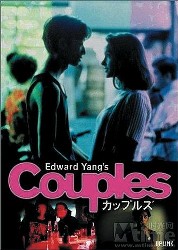
拍照。楊德昌的《
獨立時代》卻在小劇場演一段舞台劇當成開鏡典禮,特立獨行,空前絕後。往後,等到你我觀賞這部電影時,才更驚訝開鏡儀式的舞台劇只是為後來的電影熱身,既非片中的一部分,更不像整部電影的縮影。或許,楊德昌對互補的興趣遠超過「節錄」與「仿製」。
《獨立時代》與《
麻將》當年我都只看過一遍,距今為時久遠,我原本打算參考、「摘錄」自己舊稿片段轉載,不料句句都是重點,難以取捨。倒不是我見解有多棒,而是楊德昌電影的博大精深,「害」我讀出無數佳妙。《獨立時代》裡的陳湘琪與倪淑君不約而同點菸放鬆自己並體諒對方,堪稱台灣電影中最卓越的女性主義或女同志色彩的畫面,只是,楊德昌無意重複《
海灘的一天》的成就,所以這個景觀雖然美好卻很短暫,女性間不言不語勝過千言萬語的溝通共鳴,常常由於權力、利益、階級而破滅。男孩間的同性情誼也很讓人玩味:王柏森與鄧安寧的依賴/照顧關係像兒子與父親,又宛如兄弟,有時還彷彿情侶,比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人物間多了一層權術與錢財的陰影;陳以文與王維明原本一放一收,彼此互補,公司主管的介入竟使得一個受害、一個受氣。《獨立時代》像是都市眾生相,又宛如台北的一千○一夜,在人生的舞台上大家輪流當主角。本片的英文標題《A Confucian Confusion》不但字形、字音相近,相映成趣,同時也告白了孔子與儒家的侷限、身為儒者的困惑。楊德昌不想受制於孔子(或儒家),春秋戰國時代還有墨子、老子、莊子、法家、陰陽家…百花齊放的中國,才是最自由、允許更多更新可能性的中國。
英國男人認為英語可以跑遍台北、左右逢源,法國女孩諷刺對方不解中文。綸綸、「香港」、紅魚、牙膏,這四個男孩分享一切,包括女友。紅魚忙著幫助法國女孩Marthe,是想拐去賣為高級娼妓,但他不懂法語、不諳英語,要靠綸綸翻譯好讓他跟Marthe搭訕。綸綸原本被當成翻譯的工具,但他譯不出太複雜的字句或是私下同情法國女孩而故意譯得走樣。語文介入,居然反轉了原先的主從關係與優劣地位。Marthe在台北要用英語方才容易溝通,萌生的戀情卻使得Marthe學了幾句中文、綸綸學上三言兩語的法文。本片順便暗示了法語跟英語在台北暗中較勁。綽號「香港」的男孩明明是台灣人,這位假香港人後來去誘騙真正的香港(女)人Angela,不料那位中年女人跟姊妹淘大鍋炒這位少男,搞得他嘔吐甚至哀號(哀號時,畫面轉接城市的夜景,個人的哭叫延伸為台北城市的悲鳴!)。男孩子們可以分享這個女孩、那個女人,自己卻無法任由女性一次集體分享,楊德昌的女性主義思維以及女與男、名與實、性與暴力、家與國…的多元觀照,使得小品《麻將》無比豐厚,從頭笑到尾的上乘喜劇。《海灘的一天》聚焦於女主角(張艾嘉飾演)的經驗、記憶、所思所感,卻用台灣今昔多種階層、多位女性的「異」與「同」反映出多樣性,女主角的母親(梅芳飾演)與外省女孩(胡因夢飾演)刻劃得生動鮮活尤其深印台灣影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讓多位少男少女眾聲喧嘩、百花齊放。《麻將》的人物不僅本土,更延伸到法國人、英國人、香港人,楊德昌預見了台北成為國際城市。

《
一一》以婚禮揭開序幕,用喪禮壓軸。你我不免想起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有三次死亡(女主角父親的、哥哥的、丈夫的),丈夫只是失蹤,不確定是否死去,電影不交代也不在乎那人是死是活,楊德昌為台灣電影提供了「開放式的結尾」。1985年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有三次死亡(父親的、母親的、祖母的)。《一一》色彩常常簡約成紅、綠、黑、白,既潔淨又風格化,或許呼應《海灘的一天》中,映著紅色背景時,胡因夢的黑衣與張艾嘉的白衫。彩色電影的黑白對比。《光陰的故事》的短篇〈指望〉與《海灘的一天》,楊德昌都用西洋古典音樂來當配樂,美妙如詩,台灣電影以往少見,令人驚艷。就當大家以為楊德昌是古典音樂素養極高的鑑賞家或者他只愛古典音樂,不料,《恐怖份子》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竟把西洋流行音樂運用得水乳交融,讓人大吃一驚,原來他對這些同樣別具慧眼、更具深情。
《一一》讓主角男童洋洋(張洋洋飾演)的父親(作家
吳念真飾演)與日本朋友一位愛流行音樂、一位酷嗜古典音樂,互相引介給對方,各種音樂就像各類族群,楊德昌期待的是相容,是彼此尊重。《海灘的一天》那雙兄妹(左鳴翔與張艾嘉飾演)受父親強迫薰陶,可憐兮兮正襟危坐聆聽古典音樂,楊德昌愛音樂卻能冷靜觀察、批判中產階級某些人的強人所難,挖苦了父權也質疑了偽善,或者,父權的是非功過一體兩面(給你養分也剝奪你的自由權)。批判與包容,對音樂也對人、對事。楊德昌兩面靈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首曹雪芹詞、劉雪庵曲俱佳的《紅豆詞》被白色恐怖歲月警備總部(蔣氏王朝的爪牙鷹犬)人員吟唱,無辜被捕的小人物(小四的父親)聽得情何以堪?再美的音樂(或藝術)也都可能被惡勢力用來欺壓個人或族群啊!《一一》裡的男童洋洋擁有照相機以來,總是拍攝別人的頭部(後腦),理由是要呈現別人自己看不到的地方。這正是影像(或藝術)工作者開發、探索你我看不到的面向的隱喻啊!片頭演職員名單的中文一律由左向右橫排,唯獨片名《一一》從上往下直行,既是兩個「一」字,又像一個「二」字。片中跟洋洋同一輩份的男孩女孩,名字都用疊字。開場時,結婚照片被隨手倒置,別有深意。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經《獨立時代》(陳湘琪在片中是位有幾分奧黛麗赫本氣質與美貌的女孩)到《一一》都驚鴻一瞥,原來楊德昌的電影夢不僅是雷奈的《天意》與《我的美國舅舅》、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安東尼奧尼的《放大》啊!
《一一》裡的外婆死去,很超現實。台灣電影不大容易見到超現實,楊德昌處理得又好又巧妙。有一回,我問楊德昌,《
青梅竹馬》的英文片名《Taipei Story》非常切題,但中文片名我難窺玄奧。他沒有正面答覆,旁敲側擊表示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又表達了什麼?那只是第八部半電影,全然不提內容。這給我莫大的啟發:或許都長大了,不再青梅竹馬;也可能社會結構變遷,青梅竹馬的機緣不再存在。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可能並非去年,也許不在馬倫巴,不是嗎?總是記得,《青梅竹馬》裡的棒球選手(吳念真飾演)飽受往昔運動傷害的折磨,還有,女主角的妹妹看電視錄影帶快轉、不看節目,只看美美的廣告。楊德昌總是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本文轉載自破週報
張貼日期:2007/07/23
更新日期:2008/0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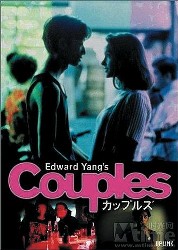 拍照。楊德昌的《獨立時代》卻在小劇場演一段舞台劇當成開鏡典禮,特立獨行,空前絕後。往後,等到你我觀賞這部電影時,才更驚訝開鏡儀式的舞台劇只是為後來的電影熱身,既非片中的一部分,更不像整部電影的縮影。或許,楊德昌對互補的興趣遠超過「節錄」與「仿製」。
拍照。楊德昌的《獨立時代》卻在小劇場演一段舞台劇當成開鏡典禮,特立獨行,空前絕後。往後,等到你我觀賞這部電影時,才更驚訝開鏡儀式的舞台劇只是為後來的電影熱身,既非片中的一部分,更不像整部電影的縮影。或許,楊德昌對互補的興趣遠超過「節錄」與「仿製」。 《一一》以婚禮揭開序幕,用喪禮壓軸。你我不免想起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有三次死亡(女主角父親的、哥哥的、丈夫的),丈夫只是失蹤,不確定是否死去,電影不交代也不在乎那人是死是活,楊德昌為台灣電影提供了「開放式的結尾」。1985年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有三次死亡(父親的、母親的、祖母的)。《一一》色彩常常簡約成紅、綠、黑、白,既潔淨又風格化,或許呼應《海灘的一天》中,映著紅色背景時,胡因夢的黑衣與張艾嘉的白衫。彩色電影的黑白對比。《光陰的故事》的短篇〈指望〉與《海灘的一天》,楊德昌都用西洋古典音樂來當配樂,美妙如詩,台灣電影以往少見,令人驚艷。就當大家以為楊德昌是古典音樂素養極高的鑑賞家或者他只愛古典音樂,不料,《恐怖份子》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竟把西洋流行音樂運用得水乳交融,讓人大吃一驚,原來他對這些同樣別具慧眼、更具深情。
《一一》以婚禮揭開序幕,用喪禮壓軸。你我不免想起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有三次死亡(女主角父親的、哥哥的、丈夫的),丈夫只是失蹤,不確定是否死去,電影不交代也不在乎那人是死是活,楊德昌為台灣電影提供了「開放式的結尾」。1985年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有三次死亡(父親的、母親的、祖母的)。《一一》色彩常常簡約成紅、綠、黑、白,既潔淨又風格化,或許呼應《海灘的一天》中,映著紅色背景時,胡因夢的黑衣與張艾嘉的白衫。彩色電影的黑白對比。《光陰的故事》的短篇〈指望〉與《海灘的一天》,楊德昌都用西洋古典音樂來當配樂,美妙如詩,台灣電影以往少見,令人驚艷。就當大家以為楊德昌是古典音樂素養極高的鑑賞家或者他只愛古典音樂,不料,《恐怖份子》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竟把西洋流行音樂運用得水乳交融,讓人大吃一驚,原來他對這些同樣別具慧眼、更具深情。